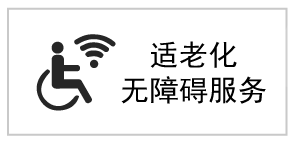土碗制作不简单
据《大足县志》记载:大足土碗业始于清代中期。据说,在乾隆年间,有广东常乐县制碗户杨、朱、卓、蔡4家迁来四川,在兴隆(今古龙)和铜梁玉峡口办碗厂,光绪年间杨姓后裔迁玉龙开碗厂。
土碗厂地点的选址须具备有碗泥巴、水、煤炭3个基本条件,而玉龙红岩沟则占尽了天时地利。玉龙土碗制作工艺精湛,在大足同行当属佼佼者。为探寻土碗的传统制作工艺,我们前往龙水湖畔的正兴街,拜访了土碗制造的见证人刘绍珍与王中富两位老人,请他们讲述了土碗制作的前世今生。
土碗的原料是一种当地人称的“泡沙石”,在玉龙碗厂附近,只有玉峰村1社的王家坡、7社的偏岩子两处的泡沙石最正宗。泡沙石比石头软得多,用铁镐像打地道似的开采,再雇村民挑下山。过去没有粉碎机,碾细泡沙石的方式尤为原始。一种是将泡沙石铺在平整的石板上,黄牛拉着大石碾子周而复始做圆周运动。另一种则是更有趣的“水舂碓”,利用溪水落差原理,冲击木轮滚动,力量传递给木锤,舂打石碓窝里的泡沙石成细沙。
然后,将细沙放入6米长、2米宽、1米多高的石水槽里,再用长木扒梳用力来回拖动,上面层是浅黄色的泥浆,下层则是细沙沉底。打开槽子上端闸门,泥浆便流进下面的水槽沉淀后,放走上面的水,剩下的就是碗泥浆了。挖出泥浆在窑上烘干后,把泥块挑入作坊捣碎,混入少许泥浆,几个匠人赤脚踩半天,凭脚掌的感觉,剔除小石子之类的杂物,让碗泥巴像糍粑一样黏稠。踩泥巴是件辛苦活,特别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天,半天踩下来双脚麻木,脚掌上长满了冻疮,疼得钻心,直到开春后才能康复。
车碗师傅把一坨碗泥巴放在直径80厘米左右的车盘上,用手柄加速摇动,车盘达到每分钟70转的速度。师傅双手虎口卡住,两个大拇指往上捏提,碗的形状就出来了。熟练师傅一天能够车400多个中号碗胚。将泥碗整齐放在桥板上阴干,切忌暴晒,更不能被雨打湿而损坏。
车碗是个熟能生巧的技术活,指头犹如钢琴家那样灵活,要用心掌握好它的速度和力度,做到碗大小一致、厚薄一致、深浅一致。要到达如此娴熟程度,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
待泥碗阴干后,逐一打磨光洁。有的在碗上用毛笔描绘出栩栩如生的鱼、梅花、兰草、鸟儿等图案,活脱脱的水墨画,让人耳目一新。釉浆是用糠壳烧成灰过滤后去除杂质,再混合一定比例的白泥浆而成。釉浆放入大铁锅里,将干了的泥碗快速放进锅中浸泡瞬间,再放在桥板上阴干。
听老人们讲,烧制土碗的窑子依山而建,就像人疲倦时睡到坡上,故名“困山窑”。窑子用砖砌成,顶部成拱形,有6个仓,每个仓可装2000个碗。装窑师为六级工,是厂里工资最高者,既是体力活,又是技术活,烧出土碗合格率的高低,装窑师非常关键。装窑最辛苦,尤其在三伏天,尽管窑子已经熄火一天,但里面仍犹如大蒸笼,全身被汗水浸泡得好似落汤鸡,许多人根本吃不了这个苦。
待碗全部装入仓后,烧窑师最后登场。开始用木材或煤炭小火,第一天为预热火,每个仓逐一加温,尔后逐渐加温至1300℃左右。当时无温度计,全凭烧窑师的经验判断,通过仓的窑门孔,勾出碗察看若变成了“丝瓜纹路”便大功告成,立即熄火。从头到尾,需要3天时间。有的烧窑师的诀窍是父传子,一般不外传他人,生怕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父”。烧窑师对火候、加煤、温度、时间几个节点的把控胸有成竹,只要留心,阴沟里翻不了船。烧窑非常劳累,加煤炭、掏炭渣是高强度体力活,灰尘又大,特别是在酷暑期间,靠近窑子,挥汗如雨。
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,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土碗销售市场逐渐萎缩,土碗烧制也慢慢落下了帷幕。
 网站专栏
网站专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