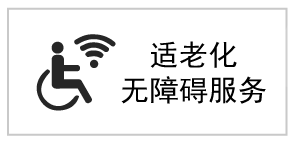入选全国创新案例!大足石刻这个项目凭什么“出圈”?
在重庆大足区的青山绿水间,散落着千百年来默默诉说着历史的中小石窟。它们不像北山、宝顶山那样声名显赫,却同样承载着灿烂的文化记忆。
近日,大足石刻研究院推动实施的大足石刻中小石窟艺术村落项目,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“2024-2025年度最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展示活动”创新案例。
这一荣誉,不仅是对一座座石窟保护成果的肯定,更是对“文物活起来、乡村美起来”实践路径的高度认可。
大足石刻研究院是如何将散落在乡村间的文物与村落结合,在山水之间打造出一个个艺术村落的?10月21日,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探访。
为散落山野的瑰宝穿上“防护服”
在大足,并非所有石刻都如宝顶山、北山般集中而闻名。还有68处中小型石窟,像被时光遗忘的珍珠,散落在18个镇街的密林深处。它们年代跨越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却因分布零散、处境偏僻,长期面临着风化、渗水、岩体失稳乃至盗扰的威胁。
“它们的‘病痛’各不相同,保护难度极大。”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道出了保护的艰辛。
守护,从为石窟建立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开始。大足石刻中小石窟艺术村落项目,正是为此而生。它为包括陈家岩摩崖造像在内的21处石窟,量身打造了坚固的保护建筑。这不仅是物理上的遮蔽,更是一次全面的升级。
更重要的是,智能安防系统的全面引入,为这些僻静的石窟配备了24小时在岗的电子“保镖”,实现了远程实时监控,安全防护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。
如何守护这些国家的宝贝?答案不仅在于技术,更在于人与制度的合力。
20多年来,大足陆续聘请了77名义务文保员,他们中有年过八旬的老人,也有正值壮年的村民。
王学豹就是其中之一,他在陈家岩摩崖造像旁守了18年,住过不足4平方米的临时棚屋,挖过数不清的引水沟,月薪从30元涨到500元,他却说:“我不是为了钱,它们是国家的宝贝,我要守好。”
而另一群守护者,则是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的修复师们,在中心主任陈卉丽的带领下,这些石刻医生在狭小的空间里细致作业,面对岩体失稳、渗水、彩绘剥落等“重症”,他们按病情轻重分批“救治”,有的进“ICU”紧急修复,有的则住进“普通病房”进行系统性维护。
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,为中小石窟艺术村落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让传统技艺与乡村记忆找到传承人
如果说保护是项目的根基,那么融合与活化则是其灵魂。
大足石刻中小石窟艺术村落项目,并非孤立地进行文物修缮,而是将石窟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,打造出一条“石窟寺+文旅”的创新路径。
项目的创新,远不止于砖石与科技的堆砌,更在于它为人、技艺与乡村记忆搭建了一座桥梁。在建设过程中,项目汇聚了建筑、文化等多领域专家的智慧,并刻意开启了“以老带新”的传承模式。
本地的能工巧匠们将世代相传的木作、石作、瓦作等技艺,倾囊相授给年轻一代。叮咚的斧凿声间,传承的不仅是手艺,更是村民心底沉睡着的那份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豪。
除此之外,在空间布局上,大足石刻研究院不仅为每一座中小石窟建有石窟保护房,还配套了管理用房、公共卫生间、步道与安防设施,形成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链。
“我们不仅要修复石头,更要唤醒文化记忆。”蒋思维说。项目通过打造“乡村石窟寺文化景点”、构建文化公园、设计文物主题游径,推动“石窟寺+”文旅产品开发,使散落山野的石窟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。
沉睡的石窟被巧妙地融入乡村肌理,化身为一处处“乡村石窟寺文化景点”和微景观。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历史遗迹,而是串联起文物主题游径、构建乡村石窟文化公园的核心要素。
大足力推的“石窟寺+”文旅产品,匠心打造的特色精品游线,让这些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化资源,成为推动当地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。
从文物孤岛到文旅融合的乡村实践
根据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,我国现有石窟寺及摩崖造像5986处,其中省级以上文保单位仅705处,绝大多数为中小型石窟。它们普遍面临保护力量不足、设施欠缺、监测困难等问题。
大足石刻所面临的挑战,正是全国中小石窟保护的缩影。
“我们不仅在保护大足的石刻,更在为全国的中小石窟保护探路。”蒋思维表示,保护的最终目的,是让文物活起来,因此,该项目从立项之初就成功跳出了“为保护而保护”的孤岛,将石窟保护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深度融合,探索出一条以文化引领乡村发展的新路径。
环境的焕然一新、文化价值的彰显,不仅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,更吸引着他们主动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,形成了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这一从“文物守护”到“乡村赋能”的成功实践,为大足石刻乃至全国众多中小石窟的未来,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的画卷。
从王学豹18年的孤独守护,到陈卉丽团队的精心修复;从散落山林的危岩造像,到融入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——大足石刻中小石窟艺术村落项目,用实践诠释了“保护不是终点,活化才是永恒”,它让千年石刻在新时代焕发生机,也让乡村振兴因文化而更有温度。
 网站专栏
网站专栏